梦到白色巨物,梦见白色的物体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梦到白色巨物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梦见白色的物体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本文目录
这是一种叫做巨物恐惧症的病,但问题不大。
巨物恐惧症”
(megalophobia),也就是非常害怕巨大的东西,看见轮船、飞机甚至是大云团都会晕倒。
巨物恐惧症常见特征是,一些平常的物体会变成大怪兽,如果盯着它们看太久,就会在它们身上看出脸来。
另外,虽然知道巨大物体会让自己害怕,但却忍不住看各种照片来折磨自己,这也是该病的一个常见特征。
无须太过于担心,没事的,梦与现实是相反的
第一幕:淋浴间
一个黝黑的少女的脸庞出现在淋浴室通向庭院的傍晚的窗户旁。
这并不是什么恐怖事件——起初芥子需要艰难地弯着脖子,才能看到一点点花丛后面的她。
但那张脸在暗沉中似乎有一刻突然地放大了——仿佛是暮色逐渐变得稠密而令它柔和地浮到窗边了一样。
芥子仍然盯着她看:水哗哗地流着,芥子赤裸着身子,探出湿漉漉的脑袋。
温热的夜令她有些发昏。
不知是水汽涨了上来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让那张脸开始模糊了起来,一会儿它彻底消失不见了。
——我要追上她。
芥子这样想着,沾湿的脚掌踏在冰凉的白瓷地板上,有一些水溢了出来。
她没有找见拖鞋,她感觉脚底痒痒的。
她很热,她感到了身体轻盈宛如一个棉絮一样——和那春风对于棉絮的那种微薄的托力。
走出浴室的瞬间,她感到仿佛冷风突然吹过一片干涸的河床——也是那些早春的初具水分的稀薄的风,拂过一张枯僵的,封存在冬季里的脸。
不知为何,她感到自己又轻盈又萧索,而那些她失去的东西仿佛都在窗外——在那个黝黑的少女那里。
黝黑的少女——幽暗而有光泽!
丰润又强健!
芥子只是看见了她一眼,但她断定她是不可思议的。
不然水汽为何能将她隐去?那时候,她像是由暮色和蒸汽调和而成的。
她像花丛一般能够蕴蓄,她拥有沉默、悄然接近和某种近乎浑厚的收敛的神秘——她类似于在一个阳光下袒露着粗糙的、淡粉色肉体的中年女人的身旁,那露出半个贝壳的小小的沙穴的守密者——她是那不可见的肉芽与阴湿的缱绻。
夜,在环绕着,紧接着是,缠裹,紧缚——被血管的荆棘所包围的心脏,搏动即是一颗晦涩之卵中的困顿。
芥子越走越感到疲惫。
她正在变得干燥——她难以忍受。
她想回到淋浴间里,但那已经不可能了:她走得太远了,白瓷砖上留下一条漫长的湿痕。
很热——她断定,即使她什么也没穿。
她感到了令她眩晕的升腾——那庭院里的风,来自她无法想象的空旷的夜的心中,正在以它空漠的闲置——那夜空是一切轮廓的收藏家,却令所有的隐蔽的、物之决意都黯然失色:那凸显着树木的威严却往往忽略着它们苦涩的生长里的全部的负担的,轻浮的夜空呵——此时也来争夺她的组分,令她稀薄,令她流失。
芥子突然渴望怀抱住什么——无论什么,比她自己更鲜活的那些——她想握住一条滑溜溜的金鱼,她想维持在它将要滑脱与勉强将它留住的紧张之中。
——黝黑的少女啊,救救我吧。
芥子向她呼唤。
第二幕:公主与骑士
少女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芥子的梦中了。
黝黑的少女降临在所有令她沮丧的,那渴望着奇遇的失意中——少女就是芥子对生活之平凡的抵抗的,某种更柔缓的面貌。
她以某种劳苦者的形象,将那不可担负的什么顺利地放在了肩上。
少女意味着在一种除去收获之喜悦的,对耕作的执着。
是转世成驼兽的猝死的汉子那人类般的眼泪。
少女是一个荒唐的承担者的姿态——她是静止、沉默、不作为——却因为那具身体给人的强烈的如同静物一般的感受与某种深藏的人性之间的冲突,而形成一种张力——人们甚至觉得,她的形象简直触及了一种使命感。
她意味着对一切飘忽不定的吸收——却仍然显得那么甘美、安稳、没有顾虑。
她是幻觉的女儿却不受它的盘剥。
少女是一个芥子用来自我安慰的形象——当她的想象抵达了什么空洞的、虚伪的事情的时候,她会欣慰地想到那些事在少女的世界中是如何如同日出日落一般平常。
芥子知道,那个黝黑的女孩早就出现在她生命里。
五岁的时候,她想成为那不乖的。
端庄的母亲一度教导她,她也曾满怀骄傲地效仿着。
但突然有一天,一种违逆的情绪萌生并迅速成长——她加入了一个顽劣的团伙(调皮的孩子们),并一起被罚站在了墙根。
她不敢看向老师,因为羞愧,而且感到一种隔阂。
此时,她热切的目光正无限地打量着她的新伙伴们——她渴望那些顽皮的孩子们给她亲人般的接纳,给她以全新的、有别于母亲的庇护。
但很快她觉察到无人能够充分地回应她这种异样的热情,他们——调皮的那些,仍沉浸在欢呼雀跃的冒险行动中,一个个对着老师偷笑。
她对他们没有太多兴趣了。
她感到他们并没有一种严肃的、团体般的相互扶持的美妙情感。
就在芥子极度沮丧之时——那名少女出现了。
在那个座位里正冲着她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仿佛就是为了她而设的,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美丽的姑娘。
她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
但自从刚才起那个姑娘就在盯着芥子——现在她变得更专注了,她的表情微微浮动——芥子感到她似乎想要有所动作:长时间里芥子忍耐着,犹豫地回应着那种专注和那引发的姿态。
惩罚结束——她跑回位置,看向她——那个女孩儿,却突然张开了双臂!
芥子不敢相信,但那个温柔而热诚地目光告诉她是这样的。
孩子们间发生的事是最接近于神话的,因为还没有什么能干扰到她们。
而我们一种美好的责任就是静静地见证这些也许有点失真感的时刻。
小芥子迎了上去,她感到之前的痛苦是值得的。
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少女已经完成了一次对她的拯救。
少女令芥子的行动变得闪耀了,她呵护了一件隐秘之事。
对于一个幼儿园孩子来讲,芥子是很特别的,她过早地觉醒了某种放置自我的决心——不论是在她母亲那里,还是她幼稚园的朋友那里,芥子已经有想法要成为别人的什么。
但仍然可以说这个时刻是危险的——当幻想在她们头脑中还很放肆的时候,她们的情感很容易成为过量的:芥子就恰好越过了边界——她产生了难以描摹的东西。
如果一种平凡的关怀还可以令少儿激发出美妙的、相互爱护的友情,那时少女的反应显然在芥子那里是过量的了。
小芥子在即将抵达那个怀抱的时候迟疑了。
那个动作已经改变了她——她借助着少女那个惊人的举动,令自己奇妙地取胜了。
小芥子借用了一个可以配得上这种荣光的形象——她是一个凯旋的骑士,她走向少女就像走向她的公主。
当幻觉继续侵占着她——令芥子感到一种谜一般的尊严的假象。
她甚至感到如果她显得冷淡——那意味着战役还未结束,作为骑士的荣誉也将继续下去;而公主,那个令人心痛的盼归者,也具有了某种残酷的、永恒色彩的东西——骑士穿越了爱的羁留呼啸而去——多么壮烈,多么值得歌颂!
小芥子就在一种愚蠢的自我感动之中完成了第一次对现实的超越。
时间与成长会改变很多事,但对芥子来说,她永远是一些幻觉的傀儡。
自从芥子再度梦到那个少女,童年的记忆随着一种更强烈的,更清晰的欲望一并回到她的生命里。
芥子体会着一种生命力的阵痛。
那种生命力——由她日渐成熟的身体与一种哲学般的,框架感与运动所构成。
黝黑的少女之面影,哑默的可怜之人——在梦中芥子看见那个饱满的脸颊,在花丛和夜色中隐没。
她想必是蹲伏着的,她注视却不警觉,她似乎有什么想要传达但是完全轻缓的,她有令芥子羡慕的存在之强烈。
那少女置入一片盈余之中。
周围的一切都涵盖着她、为她营造着她唯一的、微小而执拗的参与。
她时刻在交互着:她是自然的少女——同夜风有一项秘密的协议。
芥子觉得,那少女圆润的身体仿佛在向她周围的拥簇——那些花丛和浓雾——辐射着,类似波纹。
她同样也是无处可去的——她有着被庭院所围困的牲畜般的童贞。
芥子追赶她的时候感到某件事要发生了,要很急迫地,从那个身体里涌出——这广大的夜空,多么异常,正急速地向庭院倾注:向着少女灰暗的生命里——仿佛很快,她将鼓胀如同裹住风的袋子。
这样的形象多么地诱惑着她,让芥子瞬间体会着那将要奔赴的冲动。
少女是行动的前夕,是那仍可以被凝视、被静静地爱抚一段时间的那种填充:像曾经一度被有关公主和骑士的幻觉所占满了的小姑娘。
芥子会忍不住在自慰时使用这个形象——她感到一种滑稽的契合:想象着作为欲望与生命力的混合的某样东西,在她的内部营造着一种冲突,一种被填满的幸福感。
在这幸福的昏厥之中——芥子想到——男人是多么无力啊。
他们生硬地闯入了,却没有抵达精神的欢畅——芥子同样体会着成为一个荒唐之人的深刻的痛苦——但这也加剧了她的激情:她的可怜的、变异的淫欲呵——她想着,不存在的少女正看着她,在所有和睦的假象中开辟唯一一条通往神秘的振奋的道路:
——你懂得的,亲爱的,我的释放,我的悲哀!
那样的时刻里,芥子感到一条道路重新出现了。
——这里有可以不再行动的辩护,有凭借幻觉再度成为英雄的可能。
第三幕:葬礼
人生究竟可以这样进行下去吗?这样半推半就着,在成年人的世界上演着已经变得卑劣的童话守则?芥子感到她终有一天会将所有热情耗尽——如果少女不过是精神上的一个顽固的突起,是她羞愧的秘密与失败的人生的最后的储蓄。
芥子感到,自己的沉沦,终究与她的孤单有关。
在幻觉中沉迷的少女,与外界渐渐疏离。
但这之中也有一些关键的契机。
芥子的父亲去世在了她献给神游的16岁。
这不是什么变得颓丧的理由,但人们的离去的确意味这些什么。
曾有一个清明的晚上芥子在街边看见无数火光在摇曳。
她不禁自问:人们能从那温暖的火苗中获得些什么呢?会不会有已逝的人的脸庞,自那些小小的、急剧反应的能量堆里升起?
——多么可疑啊,在仍活在世上的人们的幻想中,与那迟滞的、空洞的、无处安放的忧虑里的一片朦胧的烟雾,在逐消隐下去的火焰的上空,散布着一种关于完结的感受:之后,人们会散去——仿佛的确受到了平抚,充斥着淡淡的忧伤与淡淡的幸福,再度变得轻盈,又美妙地回想起作为生者的愉快。
他们——火光中的人们,面色凝重或者平静的那些,动作缓慢,目光滞留在一处,或沉默或低声言语:他们都各自几乎是带着过剩的什么离开了——那已逝者早已加深了他们,令他们成为一个个隐秘的伟人的背影——而他们究竟有没有察觉?
芥子痛苦地想要声张。
她想起父亲的葬礼上,她曾面对着所有吊唁的人们,对他们的关怀表达感激——站在台上16岁的芥子,严肃的,在一种轻微的、不知所措的惶惑之中。
最后她深深鞠了一躬——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泪水将要涌出的先兆,她为此不安——她看着双眼通红的母亲,惭愧着。
她是坚强还是生性凉薄?
但她还是说服自己短暂地沉浸在那鞠躬所带来的深厚的意味之中——她尽可能地弯得很深,直到大腿处传来阵阵刺痛:那幽微的,仿佛关于命运的深层隐秘,一种内部的事业,在那里完成着。
刺痛使所有飘荡的情绪在下沉,从另一个侧面,浮上她的肉体。
每当那时——那些沉重的片刻,艰涩的、她感到需要某种修行般的劳损才能勉强度过的那些时刻——她看到自己像树的枝桠一般剧烈地生长着,向着周围扩散。
而在那个中心点上——在那个特别地时刻的全部的重担中,在她不论如何也不能付之于眼泪、以种种庸常的抒情所描绘一部神话的开端——她在那里,逐渐成为某个始源之地,成为一个小小的,神性的陶醉的中心。
一旁的堆满鲜花的灵柩里,父亲苍白的身体静卧着。
她专注地凝望了一会儿,回味着那具遗体所牵带起的一切错综复杂。
——看看爸爸,他竟显得那么小。
母亲握着她,颤抖的声音令芥子突然震悚于一个瞬间的、如同世界边缘的闪电一般的意识。
因为完全无力了,所以也不会无助——他缩小了,所以将永远是饱满的。
死者有着令芥子艳羡的完整感。
没有比一个已逝者的遗骸更令生人感到阵痛的。
但芥子想表达的是那种特殊的、如同嵌入肌肉内的石头一般的生涩的疼痛——想必已逝者,不论生前有多少遗憾,在当下也是完结的了。
他们甚至走向了一种生理上的缩小——那静卧着的苍白之体:逐渐成为雕塑一般稳固,自给自足,无所忧虑;已经再没有什么人世身份能平稳地落在他们身上——
——爸爸:已经不是了。
母亲令芥子突然感受到这荒唐的隔阂:那已经不是他了——他遗留在这里的,业已成为完结的、美丽的、缩小的;成为唯一的——向着哀乐中送别的那长长的荒唐的队伍,那些严肃而空洞的足音与垂泣——散播着一种细微的、无法分享的欢愉。
芥子竟隐约感到了那有一点可爱的、承载了某种坚定的、关于美的意志的东西赫然包裹着那具灵柩里的身体。
她同样感到难堪——因为她已经无法容忍再像女儿一般看着他,她匆匆瞥一眼那双苍白的手——竟然无比光洁,而且已经消肿了,很漂亮。
奇妙的死后身体的缩小——宛如种子一般重新回归未生发的状态。
芥子隐隐地羡慕着躺在棺材里的那个——曾经的父亲。
死者是不用费劳力的,而种子的资本也在于未成长的资本。
芥子感觉在一种隐含式的英雄主义里,英雄就类似于那死者。
——树种。
没有哪一棵完整的树的秘密是不能包藏在一颗种子中的——然而发芽即是一种残忍的跨越:第一次的微小的幼芽的冲动就能彻底毁灭它——那个圆滑的表皮,和来自沉默的、苦涩地承受着黑暗中的萌动的种子里的一切单纯闭塞。
这闭塞是英雄式的。
第四幕:少女,巨轮与雏鸟
生命之水在急速地奔流着——这不正是芥子想要看到的吗,她无比快乐地投身到每个意识的险境之中,她感到生命被充分地舒展着。
在最后的水汽蒸腾之地——芥子在淋浴间里又看到了她。
她准备充分了——她想到。
今夜,她就要追上那个少女,同她一起融入理想的乐土。
芥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
在那里,少女被特殊的、无时无刻不遮蔽着她也庇护着她的幻觉的烟气所笼罩着。
她成为可爱的无知者——她成为仅仅在一些藏匿之中,因为夜与花园的拥簇而变得异常丰沛的人;她成为那保留着闪亮的初生者的体液而长成了的人,她宛如一个没有回声的深密的矿物。
芥子追逐着她——同时看到那双如同丝绸般驯顺的眼睛:那是近乎是猎枪下无路可逃的动物的哀求的神色——同时倒映着,芥子——一位犹豫的猎人的羞愧的注视。
芥子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曾经的公主——已经忘记如何去伸手拥抱她了了么:那黝黑的姑娘,她仿佛蜷缩成一个可以放在掌中的幼小的雏鸟。
只有乳白色的、未生羽翼的胸腔在上下起伏,传递着一种令人惊骇的剧烈的虚弱感。
芥子感到振奋。
那少女是全然被动的——她委身于花丛和夜就如同她将委身于芥子。
并没有迎接那个怀抱的小芥子:她的激动在即将抵达少女的时候全部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她已经不满足于她了,拥抱意味着结局——匆匆的,模糊的,女孩儿们美好的感情的伊始——但那个时刻,依然太过衰弱了。
拥挤的渡口,被彩旗所装饰的宏伟的大船——在人声鼎沸中,穿着蓝白相间的制服的水手与士兵门整齐地排列着——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将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姑娘走出来,剪断那代表着出航仪式的彩带。
芥子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她陷入一种意识的困境:那待发的巨轮与一个姑娘之间,难道不构成着一种深重的、难以调和的、完全是悲剧性的东西吗——
一个记忆深刻的噩梦里——芥子看见自己顺着花坛走着。
她用指尖拂过那些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的大理石边缘。
一切似乎是平静的。
但危机已经从暗中酝酿了——芥子回头的瞬间,她看见一个微小的球形黑洞——那深紫色的迷蒙的中心在煽动着。
芥子很冷静——她准备镇抚那个奇异的东西。
她开始扔一些手边摸得到的东西到那个黑洞里去,她献上了一些沙土、小石子和落叶。
惊醒前的一刻,那个不可名状的东西突然膨胀了,到了夸张的地步——不过它仍然同芥子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但芥子——令她万分惊恐的是,她看到自己仍然将一些细小的东西向那个中心投掷——
那一刻,芥子感到自己是天生的被遗落者,她在剧烈的生发的面前维持了一种绝望的、无法挣脱的凝滞。
那个膨胀的黑洞类似于一个场景的扩大——一个人往茶杯中倒水,水漫出了却仍然没有停下。
它给观看者带来的不安与厌恶就是那个黑洞给予芥子的颤栗中的微小的一部分。
只不过水仍是可以被人操控的,但黑洞不行。
芥子痛恨那作为人的形体里的无助感。
当巨轮在轰鸣中驶离——人们当真能够安全地参与那个过程吗?即便是巨轮的设计者,和那些亲历了它的宏伟的组建的工人们,他们能够恰当地放置自身吗。
而那个剪彩的姑娘是最无助的——当那伟大之物出赫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要站在一个被生硬地安置的光灿的中心——到底需要怎样的心灵的解释,才能让她从巨轮的震慑中暂时脱身?那个姑娘——如果她多少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决定性的工作——哪怕是一件表面上的,也令她和巨轮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她还能够平稳地站着吗。
她难道不会惊骇于某种投身的热情,竟期待着让自己也像那陌生的庞然巨物一样奔行在海里?设计师也许可以在一幅巨轮仍是草图的回忆里安然度过那段时光,全身充斥着人类的微小的奋进的感动——但那个姑娘,芥子想要向她发问——她有什么依靠呢。
那将死于冬天的雏鸟在芥子的手里奋力地喘息——从某一刻开始,生命已经是,也永远是一场艰巨的跋涉。
那个黝黑的姑娘隐匿在夜色里,庭院成为她的世界的边界——芥子感到,那终究是她的幻觉中的少女:孤身一人,受到她的秘密的掌管——那无声的、灰暗的命运之河中细而软的水花——她的前路,一如她美丽的肌肤一般温吞,正在她幽静的身体里徘徊。
少女是没有悲剧感的悲剧——她是鲜亮却苦涩的果实,是一切的未发生;她是浸满泪水的羞怯,是被月光收割的河流的缓缓的静默——少女就是那幼鸟。
她闪动着她顺从的,而有所期待的眼睛——她不仅将自己交付给芥子,还回应了她的对那些不安之事的欲望:芥子一旦想到,少女是所有未知的苦难的前夕,是将开放在暴雨之夜的花朵的仍收敛的短暂的平静,巨大的幸福感就涌起在她的心胸——
因为她看见了——也是她不论如何努力也不能从自己的身上轻易发现的,那些预兆——成为一只将死的幼鸟的冲动和它无比真实的临迫。
艰涩地,她喘息着——当生存即是一切的时候,即便是最微小的承担将变得坚实。
那有幸在启航仪式种活下来的姑娘——那没有因为震撼而逃避也没有鼓起勇气跳下水去追随巨轮的女孩儿,也能借此在那惶然的安置中寻得一丝生机吗?但她需要变得疯癫——当那个黝黑的少女也出现在她的幻觉里,帮她完成做不到的事——当她终于被夜风占领了,美丽地被充盈着像一个濒临涨破的气球——当幼鸟的心跳在抗争中停止——巨轮旁的姑娘,希望她懂得她应付出的:她的理智。
——这多么地划算呐。
芥子感叹着。
尾声:
芥子——我们或许可以说,她是一个彻底的疯子。
但我仍然坚持为她做一些辩护——因为已经没有机会在听到来自她的声音了——那个最初的淋浴间就是她的生命最后的地方。
当警察和医生们找到芥子的时候,她正面朝下地躺在卫生间的门口,浑身冰凉。
他们很快察觉了,洗手台上放着一个安眠药的空瓶。
大家都很沉重,他们叹气,摇头,在一段时间里呆滞地注视着地板。
例行公事——很快一种严肃的、充斥着某种轻微的感动的振奋会令他们重新行动起来,医生们为她盖上白布,警察们也谨慎地到处走一走。
他们在用一种被称为“职责”的,不必过多思虑的东西来回应着她在世上的最后一点姿态——似乎也没有人能做到更多了。
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公司的同事们,一些许久不再联系的朋友们,有着几面之缘的陌生人。
他们或惊骇或心痛地听闻了这个消息。
芥子引起了人们中各不相同的、突然地降临又终会渐渐散去的一定程度的波动——
作为事实的描述应该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生,关于她死后的事情也很平常,没什么可说的。
事实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总结下来,也可能是——没什么可说的。
我甚至连芥子的葬礼都没去参加。
在一个有点奇妙的机缘里我认识了她——对于我这种三流作者来说,能有一个认真的读者也是可贵的。
芥子很快给我安排了一项工作,她带给我一些她的日记和随笔——按理说我没有义务去读它们。
但最后她还是成功地劝说了我——她说她快要死了,她最后的希望是让我能了解她一下。
我并非什么冷淡的人,但说实话,这样有压力的活计还是让我反感。
我感到芥子确实有点不同——她这人比较矫情,而且是个可怜虫,她总是显得很忧伤。
我出于作为写作者的一点习惯不想打扰她的这份状态——事实上我绝无能力参与她的心理。
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来纪念她。
我一度以为她不会真的自杀,现在就算是出于我的惭愧,我也要决定写了。
事实上很多话都是我从她的日记里摘录的,在那些梦境、回忆、还是一些带着强烈的色彩的幻觉中——我的确感到了一种文学上的亲和力。
容许我私自对她进行一点描绘——芥子有着令我惊骇的、极端的自我感动,而且她将它们全部渗透进了生活中。
她是一个难以理喻的精神负担的热爱者。
从某种程度上讲,她的确完成了很艰难的事。
所以——也算是出于我想要把这件事彻底放下的愿望,我宁愿说,这些话都是芥子写成的,我顶多算是整理了一下。
我仍然爱上了一些她笔下的隐喻,并且,在得知她的死讯之后,我试图将她的临终的生命也放到她的文字里,希望没有过度冒犯。
1、梦见水中巨物的预兆
起初难免有孤革奋斗之感,但斗志激昂,终排除困难,达到顺调,成功发达,尤能得上位之惠肋而更伸张发展。
但似乎乏其持久,耐久力,以致虽是成败交加频见,总之大体还算安然,但须防火灾或烫伤之灾。
甚好淫。
【中吉】
吉凶指数:93(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2、梦见水中巨物的宜忌「宜」宜笑对指责,宜回忆老邻居,宜不吃晚饭。
「忌」忌看中医,忌未雨绸缪,忌偏执。
做生意的人梦见水中巨物,代表经营不利,加强讲习研讨改进再重整经营。
梦见水中巨物,今天比较适合确定一些喜庆的事情哦,如果你确实有打算的话。
今天也会遭遇一些比较高兴的事情,适宜外出。
怀孕的人梦见水中巨物,预示生男,母体多保养。
梦见水中巨物,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8,桃花位在东南方向,财位在正南方向,吉祥色彩是绿色,开运食物是花生。
无论你的梦里出现的是宁静的湖水、滴流的小溪、狂怒的河流、平静的海洋;梦中的水总是喻示着生命的精华,代表了精神的洗礼和重生。
一旦你的生活变得复杂,你就有可能梦见自己遇水溺死;湖水象征着你想要尽快从烦乱的生活中挣脱出来,渴望过上宁静安稳的生活。
恋爱中的人梦见水中巨物,说明双方了解愈清楚之时,就是分离的时候。
本命年的人梦见水中巨物,意味着诸事有阻碍,慎防损伤。
有恒心可化凶为吉。
上学的人梦见巨物,意味着试题误答,未能如愿录取。
恋爱中的人梦见水中烤,只要互相信任,婚姻可成。
秋季有喜庆。
无论你的梦里出现的是宁静的湖水、滴流的小溪、狂怒的河流、平静的海洋;梦中的水总是喻示着生命的精华,代表了精神的洗礼和重生。
一旦你的生活变得复杂,你就有可能梦见自己遇水溺死;湖水象征着你想要尽快从烦乱的生活中挣脱出来,渴望过上宁静安稳的生活。
梦见自己逃跑,意味着灾难临头。
怀孕的人梦见水中捞鱼,预示生男。
夏占生女。
恋爱中的人梦见水中窒息,由时间来考验,婚期延后,可成佳配。
梦见水中,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白色,财位在东南方向,桃花位在正东方向,幸运数字是9,开运食物是荞麦。
恋爱中的人梦见水中金蛇,说明互相尊重对方,谦虚有礼,婚姻有望。
梦到自己在水中,这是一个好梦,表示烦恼着你的事就要获得解决,在工作上进展顺利。
本命年的人梦见巨物,意味着慎防损伤,水边亦小心。
外出远行注意安全。
本命年的人梦见水中人,意味着诸事不顺,健康欠佳,宜多保重。
做生意的人梦见水中树,虽然有谣言,不理它自然平息,有钱赚。
本命年的人梦见水中骑行,意味着先苦后甘,目前防小人、官司,春来开运。
关于梦到白色巨物,梦见白色的物体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文 营星解梦网 原创,转载保留链接!网址:https://www.456781234.com/H5yNnGFBMPOe.html
1.本站所有内容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2.本站内容仅做参考,用户应自行判断内容之真实性。切勿撰写粗言秽语、毁谤、渲染色情暴力或人身攻击的言论,敬请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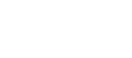






.jpg)
.jpg)